|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
[美]林赛.沃特斯 (肖福寿、唐建清 译)
全部的人类历史是什么?它们不就是那种有关天才将其无限的渴望,以巨大的能量,不断输入人体的记录吗?
——爱默生《自然的方式》
把这么多的中西方学者和作家召集起来(如我们在南京的相聚)的确要花很大的力气。为了礼貌起见,大家在一起似乎应该少谈一些彼此间的差异,要尽量达成双方的共识,也就是说要“求同存异”。
孔子极力推祟“礼”,而他的“礼”则包含了“礼貌”和“礼仪”之意。“礼”似乎要求我们抛开陈词烂调,尽量少谈那些浅显的中西文化差异,譬如汉字书写与英文书写之间的区别。中国同胞的异国情调如果你能适应的话,那么他们也许就不会把你看作“来自另一星球的弟兄”(我这里冒昧地引用了约翰。塞尔斯JohnSavles的一部电影的片名)!
谈起情感、心灵和智力等问题,我们之间毕竟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对吗?让那些处理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人去争吵不休吧!你看怎么样?
不,这样做不行。我想我们不应该掩饰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去自讨苦吃,想去弄清楚塞缪尔。字廷顿(SamuelHuntington )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预见的“文明的冲突”真正发生了。我们没必要让我们的生活去为像是预言者的亨廷顿增光;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为猎奇而猎奇,好让自己在国外旅行时能玩个痛快,因为观赏外国人的长相必定会使自己感到很开心。鲁迅曾理直气壮地痛斥过那么一种人,他们“愿世间人各不相向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同看辫子……”(《坟。灯下漫笔》)。
在下一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将空前高涨。
我们再也不能相互误会了;那种我们在低级小说、通俗杂志以及浮光掠影性的游记中所感受到的廉价的异国情调现在已经身价倍增。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探讨的是深层次的差异,这样才能弄清楚这些差异对我们能有什么启示:“中国文化”,西蒙。雷斯(Simon Leys)写道,“对我们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具有普遍真实性的各种观念是一个永久的挑战,然而实际上这也说明只有任我们自己的文化范围内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适用之处。”
我们的贸易谈判代表每年都要碰头,而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偶尔也会互访。艺术界、宗教界以及哲学界的善良的学者也许会说,我们的所有分歧与我们的共识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尽管我们已达成了不少共识,但我还是觉得以承认我们之间的分歧为好:充其量而言,我们只是属于一个整体中的互补成分。正如童谣中遐迩闻名的小胖子这个人物一样,我们这个整体也曾摔过—次大跃:要把这个破损过的整体恢复原状的话,就连皇帝的所有战马、所有臣民以及所有哲人也感到力不从心,至少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到的。
“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词在本世纪中国的先进思潮中是一个关键词,也是近千年来西方思潮的主旋律。这个词意味让人好好活着,远远超过寓言中所说的一只猫的九条命。它代表的是一种把人放在首位、极力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中国有篇谈人道主义文章的结尾时写道:
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游荡。
“你是谁?”
“我是人。”
要想领会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基本差异,最好的办法还是先考究一下这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含义。这是因为如果人文主义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了,那么在中国还是一个需多加探讨的新鲜话题。另外,我认为如果西方能够多吸收一点中国式的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 )的话,那肯定是有益的,反过来,如果中国能够更积极地采纳西方式的人文主义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照样是大有帮助的。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在南京会议上,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给与会者讲述了庄子著作中的一段故事:
南海之帝为修,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第七》
汤一介教授对故事是这样阐述的:中国的信仰体系名目繁多,但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不认为此亡是痛苦的。孔子教导说,死亡与痛苦没有联系,因为人在生前能够做的事情都去做了,所以面对死亡要泰然处之,要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如果你临死时还感到痛苦的话,这就说明你在修身养性方面做得还不够。生与死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同一个存在中的两种对立状态;人应该尽力顺从天命,这就要求人们做到“生也安宁,死也安宁”。
中央之帝独无七窍以视听食息,而待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却甚善。
“为报答他的款待美意,他们决定给他凿开七窍,结果使他一命呜呼。”
用汤教授的话来说,这则寓言表明的是庄子对顺从天命的人生的执著信念。在他看来,人类的所有痛苦均来源于纵欲,而这些“欲”与“道”“或”“天命”是格格不入的。
在南京会议上讲述这则故事时,汤教授提到其他的帝神想要给浑沌的头上凿几个洞口,其用意在于减轻他的疾苦好让他延年益寿,结果适得其反,让他死得极不光彩。
浑沌的故事很动人,也很可怕。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听起来更可怕了,因为这使人想起西方医学界一些行医的治疗手段:为了救命,医生拼命给奄奄一息的病人开刀,作气管切开术,在病人身上到处挖孔钻洞,以便空气能从洞口进入到他们的肺里,因为他们都患有肺气肿之类的疾病。这样做无疑给病人和家属都带来巨大痛苦。
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置人于痛苦的行为称之为过分的人文主义或者是过分的个人主义呢?
庄子对这种过度的个人主义早已进行过批判。苟延残喘并不代表人类尊严,而是恰恰相反。医生为了保全垂死病人的性命而采取极端的措施,这就好像溺水的人用指甲紧紧钩住离他而去的救生艇。庄子对于那种不计代价苟全性命的人文主义已作出了最好的批判。在评论庄子时,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z)写道:人类在苟全性命这种行为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把自己冒充成一个全封闭的个体化实体的致命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文主义已经被极度的、贪婪的激情所站污,其悲剧不在于生死,而在于苟延残喘。我们不是那位垂死的中央之帝,没有其他的帝王来使我们延年益寿,但贪图钱财的医生和保险公司会来告诉我们值得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
最近死于艾滋病的美国小说家哈罗德。布劳德克(HaroldBrodkey)就提供了这种在死亡面前竭力抓住生命的例子。布洛德克是《逃逸的灵魂》(The Runaway Soul)一书的作者,但他自己确实有一个失控的灵魂。他在《荒野之夜:我的死亡故事》(This WildDarkness :
The Story of My Death )中表达了对死亡的愤怒抗议,申明了他亲身感受到的生命的绝对价值。当他听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他说:“我觉得太骄傲了,我不在乎死亡。”死亡压不倒他。死亡不会是他的主人。他太清楚了;他也太自负了。他将用他的笔来对付死亡。他断定死亡对他的肉体的胜利不过是一种皮洛士式的胜利,因为,他说,“由于我的见解和信念的缘故,我注定逃脱不了厄运。”恐怕只有一个美国人会有如此受死亡伤害的感觉,才会如此唯我地想象他能够抗击死亡,而无须传统宗教信念的支撑。作为个体的这个自我同他自身之外的一切是如此疏远,这样他就成了现代社会念念不忘自我者的活标本。安德鲁。斯卡尔(AndrewScull )评论说:“这种唯我独尊,位于万物之宇宙的中心的自大感(在布劳德克的书中)到处存在。”
布劳德克同汤一介所说的故事中的中央之帝浑沌有相似之处吗?他固然没有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来满足他对抗死亡的欲望,但他有妻子艾伦,他说,她就像倏和忽一样热切地要满足他的需求,充当他与死亡决斗中的执剑者。他是一个文字之王,他自以为有一支他可以随意支配的文字大军,这支军队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他要为自己建造一个纪念碑,一座文字的埃及金字塔,这可以让他的肉体存活下去,继续他同死亡的搏斗,至少他要看看死亡是否会征服他的名望。
然而文字是狡猾的仆人。你可以凭结果来判断它们。但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对自己作出判断。布劳德克念念不忘的就是他自己的才华,这也许同于孔子所说的君子相吻合,“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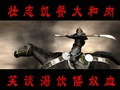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东京大屠杀
东京大屠杀
 Post By:2003/7/25 23:38:48
Post By:2003/7/25 23:3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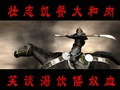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东京大屠杀
东京大屠杀
 Post By:2003/7/25 23:39:00
Post By:2003/7/25 23: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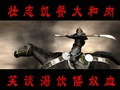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东京大屠杀
东京大屠杀
 Post By:2003/7/25 23:39:14
Post By:2003/7/25 23:39:14
